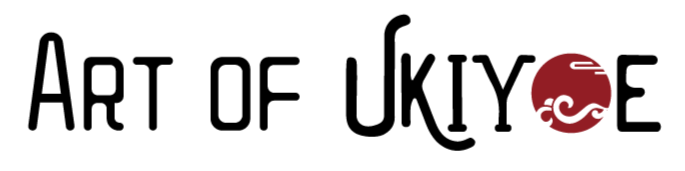鸟文斋荣之
鸟文斋荣之 Choubunsai Eishi (1756-1829)
武士里的浮世绘师|“十二头身”美人创造者|“细田派”创始者<樱花树下的美人>;18世纪末-19世纪初
如果要选一位能与喜多川歌䜆分庭抗礼的美人画大师,鸟文斋荣之也许是最当之无愧的人选、与歌䜆的肉感丰腴路线不同,荣之笔下的美人气品高洁、纤长优雅,自有一番独特的贵气之美。画中流露出的矜贵气质与荣之颇有传奇色彩的出身不无关系。
他身上笼罩着许多光环:出身于中等武士家庭,曾任将军近侍,这在以平民阶层为主的浮世绘画师群体中可谓鹤立鸡群;细田画派的开山之祖,门下有着如荣昌、荣水等同样身负盛名的优秀画师;肉笔画名家,传说他的画作甚至被天皇赏识。
荣之究竟是谁?他有哪些作品?他的作品好在哪呢?凭什么与歌䜆相提并论呢?让我们从生平和作品风格两方面入手,聊聊鸟文斋荣之的魅力。
<风俗略六艺琴>;1793-96年
鸟文斋荣之的生平
1756年,荣之生于旗本细田一族,家境中等偏上,年享五百石禄米。他自幼受良好教育,喜好绘画,师从狩野派画师狩野典信。按理说,这样的出身与平民艺术浮世绘并无交集。荣之17岁继承家主之位,进入幕府任职。25岁时升为将军随身侍从,因擅画获德川家治赏识,被委以管理画材并授从六品官位。若他一直循此仕途发展,后世便只会记得“幕臣细田弥三郎时富”,而不会认识“鸟文斋荣之”。
然而正值仕途顺遂之时,他以病辞职,转而专注绘画。正是在荣之官场得意一帆风顺之时,他却突然声称自己患病在身,不能胜任公职,坚决辞去职务,开始了作为画师的第二人生。鸟文斋荣之这一画号最早出现于天明5年(1785)前后,是他辞职隐退后的第3年。与其他浮世绘画师一样,荣之画师生涯的起点是为通俗小说绘制插图,但很快他就开始与知名的大版元合作,创作了大量美人画锦绘。
荣之进入画坛的时间点十分巧妙,恰好是美人画“改朝换代”之时。此前君临美人画界十数年的鸟居清长逐渐淡出,开始转变方向主攻鸟居派传统的役者绘;此后将要引领浮世绘黄金时代的美人画巨匠喜多川歌䜆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正在摸索自己的艺术风格。荣之在这动荡的变革之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创造出了独树一帜的“荣之式美人”,既填补了清长隐退后的空位,又在之后与歌䜆长期分庭抗礼,互相影响互相激励,一同打开了浮世绘全盛期的大门。
1789年,荣之将家主之位让给了养子(实际上的妹夫)时丰,34岁就“提前退休”,从此他不需要再顾忌身份,可以更自由地投入创作之中,这也是他绘画生涯全盛期的开始。与其他浮世绘画家不同,荣之的创作并不局限于浮世绘版画,他同时也是肉笔画名家,在富裕层中颇有盛名。1798年他宣布停止绘制浮世绘版画,将创作重心转移到了应邀执笔的肉笔画上,并专注于培养弟子,扩大细田派的影响力,直到1829年去世为止。相对较短的创作时期意味着荣之画作的绝对数量无法与歌䜆、丰国、清长等一生专注于浮世绘版画的作者相比,但其画作的质量与魅力不容忽视。少见、精致、高雅、矜贵、与众不同——如果要给鸟文斋荣之的画作做一番评价,这五个词就是理解他的最佳关键词。
<和歌三神图>;1792年
鸟文斋荣之的作品
荣之艺术生涯的前半段主攻浮世绘版画,后期则转向了肉笔画,在这里我们只讨论他的浮世绘版画。荣之的版画生涯始于1785,终于1798,只有短短13年,但纵览他流传至今的画作,还是可以较为清晰的划分成3个阶段:1780年代-模仿期、1790年代-个人风格确立期、1790年代后半-成熟期。
模仿是最高的致敬 描绘清长式美人的早期时代
1780年代,荣之作为浮世绘画师刚刚崭露头角。在这之前他学习的是狩野派的传统大和绘技法,浮世绘对他来说则是一个需要重新摸索适应的全新领域,很自然地,他选择了模仿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师——鸟居清长。荣之的早期画作是标准的“清长式美人”,有着丰润的鹅蛋脸,身形修长健美。背景描写也让人联想到清长擅长的户外群像,远景的天际线、中景的山川草木、建筑陈设、近景中的人物装饰,三者层层递进,在画中营造出了一个完整的小世界。《七小町》《风流略源氏》《十二时》《六歌仙》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但模仿者终究只能追赶前人的脚步,并不满足于此的荣之开始摸索自己的风格。
<风流略六哥仙小野小町>;1793-96年
减法美学 最优雅的“荣之式美人”诞生
经过数年历练,荣之绘制浮世绘的功力开始渐入佳境,他也厌倦了继续一味模仿清长的风格,于是他开始将自己擅长的狩野派风格融入到浮世绘之中,创造出了全新的“荣之式美人”。1790年代荣之笔下的美人仍保留了清长式美人修长的身形,但比清长式美人的头身比更加夸张,部分画中甚至达到了惊人的12头身。不仅身形更修长,荣之式美人的肩宽更窄、头小颈长,脸型也更窄长,这让美人有了类似于芭蕾舞者那样的纤弱精致感,让人联想到优雅的天鹅。在背景方面他也做了大幅修改,抛弃了清长式的丰富景物与复杂透视关系,荣之大胆选择了“无背景”或“极简式背景”,白、黄、黑等单色背景中矗立的全身美人立像或坐像是如此醒目,最大限度展示了美人的优雅气质。《青楼美人六歌仙》《福人宝合》《青楼艺者撰》《青楼美人合》这些创作于1794-1795年之间的系列画作在我看来,无疑是荣之式美学的最佳表现。
<青楼美人六花仙扇屋花扇>;1794年
《⻘楼美人六花仙》系列,也被广泛认为是荣之的代表作品之一。系列作品中特意用⻩檗等颜料染⻩的背景更衬托出身着主色调为白与紫的主人公画扇的气质高贵、娴雅与凛丽。艺伎名为花扇,身上亦着团花,手上亦持锦扇,且从她面前所置墨宝来看,又是位容姿与才学并全的妙人,观之不禁令人美之敬之。并且,还有一点有趣之处在于,“花扇”之名,亦可读作“花仙(kasen)”。
良性竞争 自由多变的成熟期
1795年之后,荣之的画作中出现了更多不同的风格尝试,与喜多川歌䜆的相互竞争意识也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比如荣之尝试了歌䜆最具代表性的“美人大首绘”,尽管数量不多,评价也远不及歌䜆,但荣之的弟子荣昌却在大首绘方面颇受好评,成就甚高。还有《美人合镜集》,一名美人手举两面镜子检查脑后发髻的样子也让人想到歌䜆爱用的美人对镜这一主题。这种竞争和模仿是相互的,歌䜆在塑造美人体态时对荣之的风格也有所吸收学习,相互竞争、相互模仿、相互竞争,为浮世绘画坛不断注入新鲜的活力。
这个时期荣之的技巧和审美风格也更成熟,各种风格路线切换自如,信手拈来。比如户外群像类的画作仍然能看出明显的清长式遗风,但背景更简洁、人物身形比例也保持了荣之式美人的纤细和更为夸张的头身比,柔美的身形弧线保留了优雅的气质,完全摆脱了早期画中的模仿感。
<丁子屋内之琴>;1790年
贵在何处?荣之美人的魅力之源
荣之的画常常被评价为“矜贵”“贵气”“精致”,这种优雅高贵感来自于哪里呢?答案要从构图、色彩、体裁三个方面去找。
首先是构图,荣之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极简背景的美人坐像/立像。刻意将构图中的“减法”做到极致,不留任何多余事物,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肉笔画的处理方式。淡极始知花更艳,绝对的简洁凸显了人物的精致优雅,也提升了作品的“格调”。
其次是色彩,荣之的画作中很少使用鲜艳的红色、橙红、朱砂等鲜艳的暖色系,而是以绿、黄、褐、紫、粉等柔和低调、不刺激眼睛的色彩为主。这种故意规避红色的上色方式被称为“红嫌”,它代表了一个审美更克制、不追求刺激而追求和谐、品味更为“高雅”的受众群体的喜好。更有趣的是这种配色方式不仅“看上去很贵”,实际上造价确实也更高。红色是所有颜料中制取最简单、成本最低的一种,而荣之爱用的紫、粉、绿造价和制作难度都更高。另外这几种颜色也相对最“娇贵”,很容易在强光和氧化作用下褪色或变色,但流传至今的荣之作品中,有不少仍然保持了鲜艳的色彩,这可能也意味着,在江户时代,购买并收藏荣之作品的群体有着相对优渥的经济条件,他们既能消费昂贵的画作,又能在数百年时光中为画作提供良好的保存条件,让珍贵的色彩留存至今。
最后是体裁,包括作品的主题和出版格式两方面。大部分浮世绘美人画的主角都是吉原游女,主题也很直白,所谓「六歌仙」「七小町」都与原本的文学典故无关,观众读者并不需要什么出众的文学素养就能轻松理解画师想表现的东西。但荣之的作品中却有相当一部分取自《源氏物语》《伊势物语》等古典文学名著。画面内容也巧妙借用了原作中的情节或象征物,对读者的素养有着一定的门槛,能理解并喜爱荣之作品的,大部分也是受过良好教育、较为富裕的人群。荣之的出版格式也与众不同,自鸟居清长之后,浮世绘很流行“x枚续”这种若干张画作拼接成横版大幅场景的做法,三张相连的“三枚续”是最常见的通用格式。荣之的作品中却存在如「两国桥下纳凉舟」这样5张拼接而成的超长画卷,这种突破常态的出版格式对工匠的技术和版元的投入都是一种考验。当我们从鸟文斋荣之的画中读到“贵气”的时候,也许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不惜工本只求效果的决心与态度。
<福船之图>;1795年
鸟文斋荣之出身于武士家庭,放弃将军贴身近臣的职位投身浮世绘的世界,这本身就是浮世绘画师中的异数。他发挥了家庭身份赋予他的知识素养、自狩野派习得的绘画技巧,创造出了气度高雅、独树一帜的“荣之式美人”,并以此为武器与喜多川歌䜆同台竞技,春兰秋菊,各有胜场。浅淡和谐、斯文克制的“红嫌”配色、纤长柔美的十二头身比例、极简背景下衬托出绝对的精致感,这一切构成了荣之画作难以抵抗的魅力。
Sharon